【文史英華】李白樂府詩中的女性形象||劉青海
歡迎關注“方志四川”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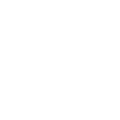
李白樂府詩中的女性形象
劉青海
李白學習漢魏詩風,其樂府詩以善于塑造鮮明的人物形象著稱。其中如俠客、謀士、游仙之類的形象,最充分地體現了詩人的個性,歷來為學者所關注。李白在女性形象的塑造方面也具有突出的成就,王安石評論李白“十首九說婦人與酒”(胡仔《苕溪漁隱叢話》前集卷六引《鐘山詩話》),雖然帶有貶義,也說明女性是其詩歌的重要主題。李白塑造了包括思婦、俠女在內的一系列女性形象,其中思婦形象尤值得研究。
詩歌中的思婦形象塑造,具有深厚的傳統。所謂思婦,即思念丈夫的婦女。思婦詩的基本主題,就是抒寫女性對丈夫的相思愁怨。古典詩歌中的思婦形象,一般可以分為征人婦、游子婦和商人婦三種。上述三種類型中,征人婦的形象最早出現。《詩經》和漢樂府中的征夫思婦之辭,是周漢以來國家征丁戍邊的產物。日本《萬葉集》中《防人歌》,也是征夫思鄉戀妻之歌,可見早期詩歌對征夫思婦的表現應是帶有世界性的普遍現象。其次才是游子婦和商人婦。漢末《古詩十九首》中游子婦的出現,和士人游學、游宦以求仕的生活方式密切相關。商人婦的形象,則是隨著晉宋以來長江流域商業的繁榮,以吳聲西曲為主要的表現形式。李白樂府詩思婦形象之所以塑造得成功,是因為他對上述從《詩經》、漢樂府到吳聲西曲的傳統都有汲取,其詩歌中的思婦形象,不僅類型多樣,而且將不同的傳統熔為一爐,推陳出新,創造出膾炙人口的名篇。
李白對征人婦形象的塑造,主要繼承《詩經》和漢樂府的抒情品格,善于選取獨特的細節來彰顯人物的內心世界,自出機杼,神理獨具。如《子夜吳歌》“長安一片月,萬戶搗衣聲”,以月下搗衣之聲為無數征人婦傳寫“何日平胡虜,良人罷遠征”的心聲,而境界之闊大,為古來所未有。《北風行》在“燕山雪花大如席,片片吹落軒轅臺”后,繼以“幽州思婦十二月,停歌罷笑雙蛾摧。倚門望行人,念君長城苦寒良可哀!……箭空在,人今戰死不復回。不忍見此物,焚之已成灰。黃河捧土尚可塞,北風雨雪恨難裁”這樣的驚心動魄之句,寫出一段生離死別之情,其奇偉壯麗,亦非太白不能有。也有受到齊梁文人擬樂府影響、風格較為綺艷的一種。如《烏夜啼》以黃昏烏鴉歸啼于枝頭起興(黃云城邊烏欲棲,歸飛啞啞枝上啼),興起思婦織寒衣、懷遠人的相思:“機中織錦秦川女,碧紗如煙隔窗語。停梭悵然憶遠人,獨宿孤房淚如雨。”此種薄暮懷人、借物抒情之機杼,深得《詩·王風·君子于役》“日之夕矣,羊牛下來。君子于役,如之何勿思”的神理,雖風格有樸質與綺艷之別,而其深于情則一。
李白在塑造征人婦時,常能別具一格。歷來表現征人婦,多突出其情苦,李白《折楊柳》則將自然春色與思婦春情相映帶,寫得旖旎多情。其中“攀條折春色,遠寄龍庭前”兩句,借游子思婦之辭中最典型的折枝寄遠意象(如“攀條折其榮,將以遺所思”),寫思婦對征夫的相思體貼之情,亦為創格。又如《獨不見》“桃今百余尺,花落成枯枝”,用夸張的筆法,將閨怨詩中常見的青春失時之嘆融入傳統的思婦怨中,可謂善變。再如《春思》,采用吳聲歌的雙關手法,表現征人婦對愛情的堅貞。“燕草如碧絲”,“絲”諧“思”,燕草生時,相思方生,如同征夫思歸之心始萌;“秦桑低綠枝”,“枝”諧“知”,秦桑低垂的枝條猶如思婦不為人知的沉沉相思。在民歌中,風吹羅帳,往往興起男女之情。若將結句“春風不相識,何事入羅幃”與“秦桑低綠枝”合看,又暗用《陌上桑》中羅敷拒絕太守引誘的故事,表達了對丈夫愛情的堅貞。所以這一位思婦的形象是鮮明而獨特的。
李白筆下的商人婦形象不多,卻個個出彩。其源應出于吳聲,但在形象塑造上有很大的發展。吳聲西曲篇制短小,對商女的塑造,多寫相思之情,并多剪影式的表現。李白自由取用吳聲西曲的形式、風格與藝術手法,創造出鮮明的藝術形象。如《巴女詞》寫巴女對遠出丈夫的惦念,采用五言四句的形式,寫出巴地特有的風土、生活與情感,是典型的吳聲體,風格也逼肖六朝民歌。《黃葛篇》寫女子采葛縫制暑服寄給遠在日南(今屬越南)的丈夫,寄到時已是秋天。末二句“此物雖過時,是妾手中跡”,寫出夫婦婉孌之情,與《古詩十九首》“此物何足貴,但感別經時”有異曲同工之妙。《江夏行》《長干行》則取法《西洲曲》,衍為長篇,為年輕商婦寫照。《長干行》尤為絕唱,開篇敘孩提時青梅竹馬、兩小無猜之情,接下敘兩人婚姻生活的來歷,逐年敘下,句法本于《古詩為焦仲卿妻作》而變化之。但古詩濃厚,語多怨嘆;而太白此首倩麗,情意纏綿,想象瞿塘風波險惡一段,尤見相思情深。由“一一生綠苔”接“苔深不能掃”,又引出“落葉秋風早”,頂真之妙,雖天然風謠不能過。至“早晚下三巴,預將書報家。相迎不道遠,直至長風沙”則空際傳情,與遠人對語,蓋思念之極,不覺如在目前。吳聲《子夜歌》“想聞歡喚聲,虛應空中諾”,正寫此種情狀。同樣是表現對丈夫久別不歸的思念,《長干行》寫相思之深,《江夏行》則抒久別之怨,如“不如輕薄兒,旦暮長追隨。悔作商人婦,青春長別離”,牢騷之深,轉見相思之苦。《荊州歌》“白帝城邊足風波,瞿塘五月誰敢過”,也表現商婦對丈夫遠涉風波的牽掛與擔憂。但和《長干行》中商婦終日相思不同,這位商婦尚需養蠶繅絲:“繅絲憶君頭緒多,撥谷飛鳴奈妾何。”“絲”和“緒”皆用吳聲最常見的雙關手法,而以布谷之聲傳寫思婦盼歸之心,皆能得吳聲歌之神理。
李白筆下的游子婦形象,與他一生的漫游經歷相關。其對游子婦的塑造,以古意、擬古、自代內贈之作為主,主要的形式是五言古詩,樂府代言之作較少。故其樂府詩中游子婦的形象,不如征人婦、商人婦那樣豐富多樣。但李白畢竟是樂府大家,其樂府詩寫征人婦的代表作,仍對傳統的游子婦形象有所發展。征人衛國戍邊,大義所在,而邊地勞苦,生死難料,歸期不定,所以詩歌中的征人婦,多表現其相思之苦。游子遠行不歸,則主要出于功名之望,有時還會出現心有他屬的情況,所以歷來對游子婦情感的表現相對復雜,以相思為主,時或夾雜猜疑,如《古詩十九首》“浮云蔽白日,游子不顧返”“客行雖云樂,不如早旋歸”,柳惲《江南曲》“不道新知樂,且言行路遠”等。李白《白頭吟》、《久別離》皆敘丈夫負心故事,塑造出忠于愛情卻被丈夫辜負的游子婦形象,其敘事之復雜、情思之婉轉,又遠過古詩。《白頭吟》以雙鴛鴦起興,歌頌堅貞的愛情,發出“寧同萬死碎綺翼,不忍云間兩分張”的高唱,接敘“丈夫好新多異心”的故事,感慨“兩草猶一心,人心不如草”,寫出卓文君的愛情理想。“莫卷龍須席,從他生網絲。且留琥珀枕,或有夢來時”四句,在忠貞剛烈之外,又為其多情寫照。《久別離》以“別來幾春未還家,玉窗五見櫻桃花”發端,以眼前之景觸發相思之情,正是古詩最典型的筆法。“云鬟綠鬢罷梳結”,即《詩·衛風·伯兮》“自伯之東,首如飛蓬”之意,以無心梳洗為相思寫照,乃塑造思婦形象的經典手法。李白更進一步,接以“愁如回飆亂白雪”,將驚聞情變后一夜變白的亂發,比作被狂飆怒卷之白雪,仍用《白頭吟》故事,而意象之奇,則迥出于古詩之上。最后以行云比游子,愿東風吹其西來,然“竟不來”,風吹花落,今春又去,思婦也好,游子之愛也罷,亦如落花萎謝,寂寞無人知。開頭、結尾,皆情、景婉轉相生,正是古詩之法。
總之,李白樂府寫兒女情事,皆從胸臆中流出,縈回曲折,一往情深。其筆下的思婦形象,無論征人婦、商人婦、游子婦,都能在深汲傳統之源的基礎上出之以自家面目。李白在這方面的獨特成就,古往今來,恐未有能出其右者。
來源:《光明日報》 2025年11月17日第13版
作者:劉青海(北京語言大學教授)








發表評論 評論 (3 個評論)